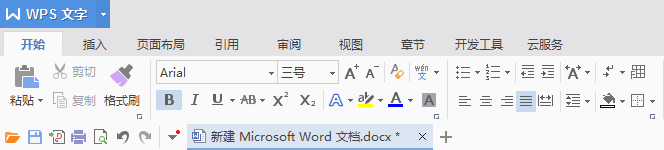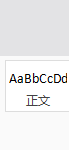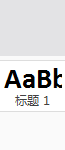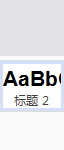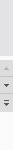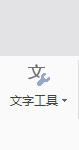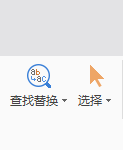一张棕色的大脸逼上面前。
我吓一跳。原来是张面具,白色长眉毛、长胡须,还有一头冰霜般的白色长发。我绕道想避开他,他居然伸手要抓我,我快走几步回头看见他提起碎花长袍在蹬跳,旁边的人都笑起来,好像是在笑我。广场上各种语言、各种口音朝我一直涌过来。今天的活动真的结束了。我似乎看到“拉达克假期”的另一对夫妻,但他们没注意到我。然后那是贾扬特吗?快门声咔嚓咔嚓,那个身影一闪而过。旁边的老妇人边摇转经筒边念念有词。这里真的太挤了,我感觉不大舒服,想办法穿过人群。
“捐钱吗?”广场边一名喇嘛对我大声喊。
我看过去,直觉地皱眉,摇摇头。
那名喇嘛笑着转头继续和旁边其他喇嘛聊天,桌上的经书被风吹开一页页在翻动,然后没人再理会我了。我继续逆着人潮往里头走,一名小喇嘛吹着口哨,扛了个比他上半身还要巨大的鼓,另一名小喇嘛从后方蹿出来打了他的头就跑。他扛着鼓摇摇晃晃追上去。我跟在他们后面走进中庭,房门外一个个斗笠都用红色花布包好了,像是等待送上输送带的行李箱。我在地上看见一本英文课本,封面黑白图案底下的名字栏位没有填上,不知道是谁弄丢了。又一名小喇嘛冲过来把它抓进怀里,边甩弄缠在肩臂上的红布巾边往后边跑出去。山坡上一间间屋宅都开着窗,我探头进去想看清楚。让一让,让一让。有几个喇嘛正搬桌子回来,他们比画手势要我更靠边一些。我贴向墙面,头顶落下一阵黄沙。两名喇嘛站在阳台合力甩动红色袈裟。我咳了起来。那名小喇嘛还在往上跑。他跑得好快,沿着步道来来回回,直到山顶上露出风马旗——
列城宫殿的画面闪过我脑中,还有达瓦。
不对。我强迫自己停下来。
我在做什么。我究竟……想要去哪?
太阳西斜,跨不过周围的屋墙,变得阴暗的广场上游客几乎走光了。我想只能等明天上午再把握时间过来看面具舞了——在这个自由之地。唰,唰,我注意到有名喇嘛在广场中央转圈。他转了两三下,暂停,折回去。他踩在一个白色旋涡的中心,而那个图腾像是蜘蛛网往外扩张,占满整面广场。他又开始转了。唰,唰,唰,唰,他一身红色袈裟连同两手飞出的长袖一起旋绕,仿佛变成一个带穗的红色陀螺。他的脚边扬起尘土,朝我越转越过来。我渐渐看不清他的脸孔……
注释:
[1] 哪会遮紧,闽南语,怎么会这么快的意思。
34
哔!
主机壳上的红灯一闪,风扇的嗡嗡声跟着推上来。
“蔡医师吗?”我将手机贴紧耳边,评鉴委员们全看过来。一定是刚才铃声突然大作。“我是雅慧,你赶快过来。”“怎么了?”电话那头的她说得很急。我退向护理站墙边,评鉴委员们继续往保护室走。“郁璇有状况。”“什么?”“她刚在厕所suicide attempt(企图自杀),你快过来,我先把她隔离在小教室。”雅慧背后听起来有些骚乱。“好,我马上过去。”
朋城椅脚的轮子像是打滑般转半圈。他从主机旁坐起来:“弄好多天了,但就,还是很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
“嗯?”我抬起视线,眼角余光感觉底下开机中的机壳还在闪灯。笔记本打开在我大腿上。
“我的自传啊,刚不说要请你帮我看一看?”朋城有些疑惑地看向我,“月底就要跟其他备审资料一起送出去了。”
“哦对,对。”
他继续看着我。
我有一点不自在,应该是第一次和病人在电脑教室会谈的缘故。大教室里如盈的声音稍微传进来。“那个——”我开口的同时他也出声。我示意他先说。
“你……是不是还没吃饭?”他问。
“嗯?还没。”
他点点头,像是看向键盘。“你们……工作也蛮辛苦的。”他稍含糊地说。
“呃,是啊。”我向他苦笑。刚才急忙进来日间病房,隔着窗看到还有一碗烧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放在我桌上,应该早已经冷掉了。如盈在讲台上看到迟到的我时也有些惊讶。“不过,和你这边都约好了,之前我说过的,我会尽量。对不起,刚迟到这么久。”
他抿嘴摇下头。
荧幕出现水蓝色的底图,“欢迎”两个字旁边的圆圈像是没有终点地一直转。“也许,我们今天晚一点结束?”
圆圈继续打转。他没有反应。
“你觉得呢?”我继续说。
他像是忽然回过神,看向我,隔了一两秒才“嗯”了一声。
我迟疑地也点头。
终于进入桌面,画面右下角的常驻程序一个方格接着一个方格地缓慢出现。
朋城隐约叹口气:“医生你刚才本来要说什么?”
“噢,没什么,只是想问你,那个自传你已经先打了一些是吗?”
“……对啊。”
我感觉他的语气有些沉重。
防毒程序跳出过期的信息,他熟练地将视窗关闭。“可能也是还要分心准备身心障碍的甄试,所以……不知道,感觉个申这边,机会没有很大。”
“是吗?”
他点点头。“但,还是会试试看啦,如盈老师还有芳美护理师也都这么说。”他比较明显地又叹气,弯下腰,插上随身碟。
教室里其他电脑都没开。靠我这儿的另一面荧幕,走道对侧的那两面荧幕,往前面一排,再前面一排,像是排列成矩阵的一个个黑洞……
砰砰砰砰。我在阶梯上两步并作一步,踩在脚下的悬空木板仿佛随时都会塌陷。为什么会这样。药物剂量已经又往上调了,也与安置机构保持密切联络,还有什么能做的?不会的。不会和之前那个女同学一样的。要怪就怪检察官居然会不起诉。我开始感到有些喘,眼前闪过郁璇父亲的笑脸——不对,他根本从没在这出现过啊。我推开大门,小教室的窗帘被拉得没留下任何缝隙。我快速穿过大教室,一张铁床被摆放在小教室门外。我转开门把。
荧幕亮起惨白,朋城点开Word文档了。我转头看向朋城。
“你直接看再说吧?”他说。
我以眼神向他确认。
他把鼠标推过来:“反正……迟早要给人看的。”
“嗯,也是。”
我把椅子稍往前滑,拿着笔的同时抓向鼠标,指尖传来一点凉意。
第一段,他的姓名、出生地与家庭背景。似乎没什么特别的。第二段,小学时的经历——整段都只有小学,全是我没听他说过的优异表现,学业成绩、班级活动、国语文竞赛……我看向朋城,他简直比我还专注地盯向荧幕。我忽然觉得不大熟悉这张脸,应该是灯光以及角度的缘故——手机突然响了。
“呃,对不起。”我从医师服口袋抽出来。是急性病房。刚急忙过来忘了切换成振动模式。“我接一下好吗?”
朋城向我点个头。
“蔡医师,我们三〇病房现在方便讲话吗?”我说简短可以。“不好意思刚那个new胚醒过来还在躁动,要不要再补一套H加A[1]?”
“好。”我向电话那头确认刚才医嘱都有开到,结束通话。
我将手机调成振动后放回口袋。这样应该没有问题。应该。我抬头发现朋城在看我,他好像想说什么。
“嗯?”我问。
他摇摇头。
“呃,那我……”我指向电脑屏幕,“继续看?”
他点头,也看回荧幕。
我握回鼠标,食指在滚轮上一顿、一顿……
“郁璇,郁璇,我是蔡医师,你可以帮助自己冷静下来吗?”我让声音尽量低沉、和缓,“来,你可以的,这阵子我们都有讨论过,记得吗?放松,慢慢来。”我看着她的眼睛说。她瞪大的双眼像在看我又不像在看我,肩膀有如抽搐般起伏,间歇露出脖子上几道新鲜的勒痕。雅慧手里拿着一大一小两个白色塑胶杯,向我使个眼色。
我瞄向朋城,他应该没注意到我又分神了。我提醒自己专心,不能再犯上次会谈时的错误。
我的手回到笔记本上。朋城转过头来。
“所以,你目前先写到这里?”我问。
“……算是。”
我点点头。“在我升上初中不久后,”我念出屏幕上的最后一段,“我脱离了学校的生活,当时我还不知道那叫惧学,或者说忧郁症。”
他“嗯”了一声。
我看了他一眼,继续念:“直到后来我被带去看医生,从那一天起,我隐隐约约明白,我的人生……注定会和多数人不一样了。”
那一天。他第一次被带来医院的那一天……
“其实光打到这边都……”他摇摇头,“这一段我已经来来回回修改过不知道多少次了。怎么写都觉得……怪怪的?不知道怎么讲。你看,我连抑郁症三个字都这样写进去了。”
“我记得,你好像并不是很……”我思索一下措辞,“认同这个病名?”
他皱眉想了几秒:“也不完全这样说吧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