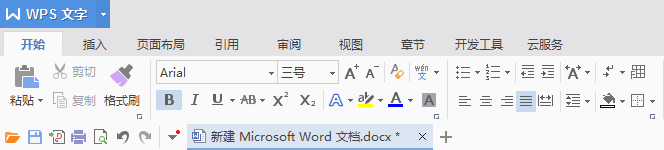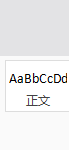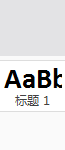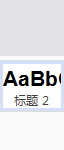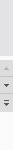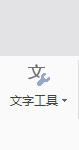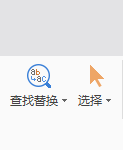魏莱是一个非常讨厌拖泥带水的人,一旦她做出了选择,那么她就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去解决问题。
她很清楚她和杜云旗之间产生的问题是不可调和,既然这样,长痛不如短痛。但杜云旗的想法恰恰相反,他希望通过拖延时间来改变魏莱的想法。在他看来,夫妻是一体的,遇到问题的时候应该共同面对,互相理解并尝试接受。
从父母回家后的当晚,魏莱就计划起了出国的事情,因为签证的问题,她最后决定去第比利斯,此前她听陆霖提过那个位于亚洲西部的城市,她又做了一番攻略后便订下了次日出行的机票。
机票订好后,她和杜云旗说了一声,杜云旗沉默半晌才说了个好字。
次日,魏莱独自去的机场,要上飞机前她给陆霖打了个电话。
“这么突然?杜云旗和你一起?”陆霖问。
“他哪有空?”她上了摆渡车,“行了,到了再给你报平安。”
陆霖觉得有些不对劲,但魏莱已经把电话挂了。
和每一次旅行一样,魏莱都一条毯子裹到身上,然后望着隔板外的云海发呆。当年,她和陆霖成为朋友的第一步,就是因为两个人都爱发呆。不是那种随时能回神的发呆,而是陷入自己的世界里,神思在另一个时空里遨游。
三个半小时,飞机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平安降落。前往第比利斯,在这里中转。中转时要等几个小时,坐在VIP休息室喝咖啡时,魏莱突然特别想去看看她的母校,想去看看她和杜云旗第一次牵过手的林荫小道。
那一瞬间的强烈冲动支配她放下咖啡拿出了手机,也巧,她手指伸向APP准备办理改签时,杜云旗的电话打进来了。
“我猜你这会儿在喝咖啡。”他笃定而随意的语气。
“嗯。”魏莱靠到座位上。
“什么时候回来?”他问。
“不回来了。”她玩笑的语气。
“好,找个你喜欢的国家,我们去定居。”他略认真。
魏莱轻笑:“你舍不下你的学生。”
“没有你重要。”他说。
她抿了抿唇:“好,我在北京等你,你现在就来。”
电话那头的杜云旗顿了一下:“我明天有个会议很重要,后天一早出发。”
她的视线落在咖啡杯上:“我开玩笑的。”
“老婆。”他语气微急,“你等我一天,我后天就来。”
“矫情了啊,演电影呢,我打个盹就继续空中飞行了。行了,你好好搞你的项目吧。”魏莱将声音再压低三分,怕扰了旁人的清净。
“我们已经很久没有一起旅行了。”杜云旗带了几分感慨。
“是啊,你忙嘛,只有我是闲人。”她拔弄着额头的碎发。
“对不起,是我没时间陪你……”杜云旗话说了一半,那边就有人急声喊他,“有点事情,我先挂了。”
“好。”魏莱应了一声,电话那边的声音已经断了。她愣了一下,拿下手机放到桌子上,抿了一口咖啡,真苦哇。
后来魏莱想过,那天杜云旗如果不顾一切的飞到北京,和她一起去了第比利斯,他们之间到了后来是不是就会变得不一样。
她无从知道答案。
真实的生活总是这么操蛋。杜云旗有他的工作,在属于他的既定的轨道上,他但凡还有一点理智,都不能做出不顾一切买张飞机票去追老婆的举动。
魏莱去了第比利斯,在隔隔海的另一个国度,她一个人去生命支柱大教堂,一个人去西格纳吉的红酒小镇,在视野无限好的半山腰餐厅,她自己喝红酒。她和不认识的异国客一起结伴,一起欢笑。
去圣三一教堂那天,她途遇一个同样来自中国的七八岁的小姑娘,小姑娘和父亲一起来的。父亲在酒店睡觉,她偷偷溜出来闲逛。出于安全考虑,魏莱便和她一起结了个伴。
小姑娘聪明,漂亮,古灵精怪,典型的别人家的女儿。
几个小时的相处后,魏莱自然而然地在心中作了个假设。假设她和杜云旗也有一个这样的女儿,那会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?
她的答案是否定的,养育一条生命是责任极其重大的事情,她目前只能做到对自己负责任,完全没有办法对一条新生命负责任。
况且生活是残酷的,大多数的美好都是稍纵即逝的,剩下的便是一地鸡毛和鸡皮蒜毛。
小姑娘的父亲找来时,小姑娘礼貌地问她能不能留下一张合影,魏莱拥抱了她,但拒绝了她拍照的请求。
除了必要的报平安,她连手机都不从包包里拿出来,她也不带相机。在旅行的时间里她从不拍照,更不发朋友圈。
陆霖曾好奇地问过她,是怎么可以忍住不拍照,不发朋友圈的。
她说,没习惯。
她喜欢用双眼记录旅途,那些去过的地方,见过的风景,遇到的人,都刻在她的脑海里。
她太喜爱自由,憎恨一切的行式主义。
然而,她又追寻归宿感。
她注定是矛盾的。
魏莱和小姑娘告别后,她破例发了圣三一教堂的风景照,随即陆霖给她秒赞,她顺手点进了陆霖的头像,进入了她的朋友圈。
陆霖朋友圈发得也不多,基本都是关于她儿子嘟嘟,或者一些有趣的事情。她从没见她在朋友圈抒情或感慨过什么,不像她认识的另一些朋友,在咖啡馆小坐片刻都得发张自拍,再配上岁月静好的文字。
陆霖最近的朋友圈停留在两天前,她的弟弟和弟媳来了昆城,她发了几张合照。照片上,陆霖搂着沈北黎的肩,两个人都冲着镜头笑。
魏莱记起来,陆霖说过她弟和弟媳妇来昆城检查身体,她有点想问问检查的结果是什么,但又不大想浪费时间在聊天上,这么想着,她便收起了手机。
陆霖这几日都心神不宁的,她弟陆城和弟媳沈北黎因为检查身体来了一趟昆城,各种各样的检查做下来足足花了两天的时间。本来陆霖安排了一大家子去温泉酒店放松放松,可巧陆城负责的项目出了点纰漏,连检查报告都没拿全,两夫妻匆匆买了高铁票回了冰市。
拿报告的头天夜里,陆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。她想着魏莱,想着弟弟弟媳,又想到自己和陆雪雅。
“怎么了?又在想选题啊?”周文恒打了个哈欠问她。
“文恒。”陆霖拉了拉丈夫的手。
“嗯?说吧。”周文恒伸手搂住了她。
“你怎么看待婚姻中没有孩子这件事情?”她问。
“这是个人选择的问题,我认为只要夫妻俩都同意,跟其他人完全没有关系。怎么了?魏莱是不是被逼生孩子了?”他说。
“是不是不生孩子就不是完整的一生了?”她又问。
“你啊,别瞎操心别人家的事情了,每个人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。”周文恒低声道。
“跟你说话真是扫兴得很。”陆霖伸手关了灯,有些烦躁地拉了拉被子:“睡觉。”
周文恒没说话,只是往陆霖身边靠了靠。老实说,他对丁克这件事情没什么看法,这离他的生活有点儿远。假设他和陆霖其中有一个人不孕,他是可以接受不生孩子的。但在身体正常的情况下,他认为孕育一条新生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。
陆霖闭上了眼睛,明天就要去帮北黎拿报告单了。她心里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,北黎的身体可能有点问题。要是真有问题……她想到她妈妈,觉得有点头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