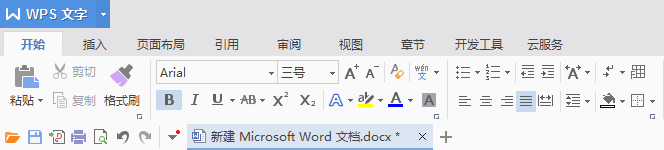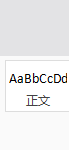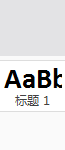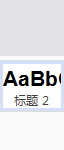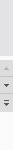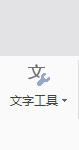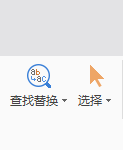树荫下蝉声聒噪。
凝望着萧家废墟前的那帮人,黎墨顿感厌恶。
亏父亲还想着对你萧家手下留情,现在看来……你们根本不值得他这么做!想要联手斗垮黎家?你们的如意算盘绝对不会得逞的!
微眯着眼,黎墨目光平淡地望着对面街道上的黎楠、萧破军和龙潮云,见他们还未发现自己,便将手中的麻绳一挽,手心立马出现一道暗红色勒痕。
回过头向板车上的两具尸体望去,黎墨目光淡漠道:“想要得到好的归处?休想。海腹荒野才是你们该去的地方。”
从众人的重围中徐徐退了出去,黎墨拉着沉重的板车,一路向海边而去。
街道上起了这么大的喧闹,萧破军三人只专注于谋划黎家,竟一个也没注意到街道为何喧哗;也正因为黎墨不曾将萧家姐弟的尸体留在街道边的树荫下,萧破军三人才完全不知道……自己刚刚的对话,其实已经被人知晓。
※
天色将夜。
黎追阳在大堂中来回踱步,几度向渐黑的外面望去,却依旧不曾看到少年回来的身影。
坐在桌旁的唐晁好不容易决定喝上一口茶,却被眼前人来回晃荡的身影扫得心烦意乱,将茶盏掷到桌案上,深吸一口气却憋在胸前不肯吐纳出来:“我说你一个当爹的,怎么能让自己的孩子独自去干这么危险的事!”
“也怪我考虑不周。”黎追阳面色惨白,一脸懊悔,眉头就像被锁住一般,紧紧皱在一起,他语气焦急:“毕竟实力上相差了两个大的境界,墨儿想逃脱怎么可能如我说的这般轻松?”
“我出去找找,唐晁,你先帮我照看一下这个家。”
“你这破破烂烂的家现在有什么好照看的,我和你一起去找墨儿!”话刚说完,唐晁拍桌而起,正要出门。
远处昏暗的视线中,少年拖着疲倦的身体走了出来。
二人见是黎墨,争先恐后迎了上去,目光炽烈地将他全身上下好一顿检查,弄得黎墨一阵好不适应,想要挣扎,却又怕损伤舅舅父亲的诚挚关怀,于是只好任他们在自己身上翻来覆去一阵折腾。
再三确认孩子完好无损,两人才各自先后松了一口气。
不过责备声却也因此响起。
“晚儿现在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,你如果再出些什么事,我唐晁就不用活了!”唐晁率先抱怨道。
“怎么去了这么久?”黎追阳倒是神色淡然,等唐晁这急性子说完,才徐徐开口问道。
“抱歉,”抱拳低头致歉,黎墨的面色有些愧疚:“让父亲和舅舅担心了。”
“萧蕾玉和萧梁岳的尸体,你送到了?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你把他们送到哪里去了?”
“海里。”
唐晁突然笑起来,爽朗地拍了拍黎墨的脊背:“这才是我的好侄子,随我性子!那两个坏家伙哪里值得你们送回去,葬身鱼腹都算是便宜了他们!”
“不像某些人,”扭头用眼睛瞥了瞥黎追阳,却又不是用正眼看,语气里带着嘲笑说道:“做事优柔,总想着给敌人留余地!”
殊不知唐晁这句话,却将一段陈年悲惨回忆重翻出来。
这段回忆,也正是黎追阳多年来郁结心中,始终过不去的坎。
这句话在黎墨听来,分明是一句不算太重的话,在黎追阳这里,却如同千钧巨石砸中心脏。
身子猛然一颤,黎追阳平淡的神情上突然浮现出一抹痛苦神色。
对啊,做事优柔寡断,才会总给敌人留下反击的余地。
黎追阳啊黎追阳……
你先用这份优柔害死了自己毕生的挚爱……
后来又害得唐柔临产之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!
两个女人把终身托付给你,却都因你而死,你可真是一个好丈夫。
注意到黎追阳脸上不对劲的恍惚神色,黎墨认真地望着唐晁:“舅舅你说什么呢,父亲宅心仁厚有什么错?”
“宅心仁厚?”唐晁也不知是吃错了什么药,只要一提到黎追阳的优柔,便由心底升起一团无名怒火,望着眼前呆怔的中年大汉,嘴角尽显讥讽嘲笑:“呵……黎墨,你可知道,正是你父亲这种所谓的宅心仁厚,才使你母亲离世的?你可知道正是你父亲这种所谓的宅心仁厚,才让这偌大的黎家基业在他手上损折了一半?!”
穿堂风自院外吹来,使得大堂变得凉意袭袭。
……
……
在黎墨出生之前,有一段故事,是黎墨从不知晓、也从听人未提及的。
他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叫唐柔,在生下他当天,难产死掉的。
但是。
黎墨却不知道,自己的母亲的死,其实还有一个其他不为人知的隐情。
……
……
谈到黎追阳的优柔,唐晁终于忍不住再次将他和黎追阳之间多年的心结摊出牌面!
黎墨也从未想过,平日与自家父亲虽小吵小闹却关系密切的唐晁,竟然有一天也能在自家父亲面前,表现得如此怒不可遏!
“如果我当初知道你一开始就已经和那种惹不起的东西扯上了关系,我就是死,也不会同意柔儿嫁给你!”
黎家十几年前那场灾祸的起因,似乎正是由唐晁口中“惹不起的东西”引起的。
当初唐柔临产,整个黎府却因那个“惹不起的东西”,遭到华夏大地一股强大势力的包围,黎府众人进不可进、出不能出,致使唐柔生产时突然血崩,无法及时就医而死!
唐家之所以这么多年未和黎家翻脸,全是因为唐柔临死前留下的遗腹子,黎墨。
“我原本以为这么多年,你已经吃一堑长一智,把自己这份宅心仁厚改掉了,”唐晁一把抓住黎追阳的衣领,眼角噙满因激动涌出的泪水,挥手便要将陷入呆滞地黎追阳打醒:“可没想到今天,你的这份优柔寡断,又差点把自己儿子葬送!”
听着唐晁这番话,黎墨只觉得自己的眼角肿胀得难受,他只知道自己的母亲是难产,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对唐柔之死的愧疚中,今天得知自己母亲当初命不该绝,心里更加难受!
黎追阳的嘴角红肿起一块,口齿间淌出一片淤血。
他斜着头,目光空洞,任由唐晁死死拉扯着自己的衣领却颓然不挣扎。
“你饶恶人,恶人未必饶你!活到这么大一把岁数,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懂吗?!”
黎墨听到唐晁这番话,却心下一颤。
父亲原本也是准备饶过萧蕾玉、甚至可能饶过萧破军,对方的这份心思,作为父子,黎墨还是感受得到的。
但还真应了唐晁这句话。
并不是所有人都应该被原谅,也并不是所有人,都能得到原谅。
至少坏人不应该,也不能。
居心叵测的人更不应该,同样也不能。
萧破军四兄弟心胸狭窄、作恶多端;黎楠明蛰暗伏、心存歹心,都不值得被原谅。
院中树影婆娑,浓郁的枝叶经风吹拂,沙沙响着——这也是这半刻钟来,周围响起的唯一声音。
“哈哈哈……”黎追阳自嘲的声音有些自暴自弃,他仰头大笑,头发散乱地粘连在额头上:“是啊,自己这份优柔接连害死自己的两位妻子,按理说……以后应该不会再犯……可你终究还是犯了!”
“黎追阳,你跟我来!”唐晁揪着对方的衣领,像提着一具失去灵魂的躯壳般向大堂外阔步走去,黎墨紧随在二人身后,寸步不离。
唐晁的步子很稳也很急促,提住黎追阳衣领的手也青筋暴露,面色更是凝重。
此时的唐晁,早已不是黎墨平日里接触到的那个和蔼可亲的舅舅。
而这个被唐晁拽住、颓然不振的男人,又何曾是他向来熟知的父亲呢?
抬头凝望夜空,黎墨静默注视着西南角那颗最亮的莹星。
它一闪一灭,悄无声息地悬在夜空中。
母亲,你知道吗,父亲和舅舅都很爱你呢,他们从未忘记你……
黎墨……也很爱你。
可是黎墨并不知道,自己父亲此时的这副颓然,更多却是因为另一个女人。
一个,如山水画般写意脱俗的女子。
三人步履匆匆,黎墨共向前走了六百三十二步,一直行到黎家祠堂。
唐晁破开大门,便毫不顾忌地将黎追阳往地上一扔,任由他向一摊烂泥一般倒在地上。
看着自家父亲这幅样子,黎墨心里也异常难受,握紧双拳静默向唐晁看了一眼,便要蹲身将自家父亲扶起来。
伸出手将黎墨拦住,唐晁厉声制止道:“黎墨,你别管他!”
唐晁大步上前,恨恨地将黎追阳从地上提溜起来,咬紧牙关指向眼前垒成小山的黎家先祖牌位:“你睁眼,睁眼看看!“
“这祠堂里面供奉的所有人,有哪一个允许你对敌人留情?!”
黎追阳没有喝酒,眼睛里却满是微醺醉意,他脸上挂着早已麻木的笑容,扫视着眼前排成小山丘的先祖牌位。
“你再来看!”唐晁转身低头,向最下一排左边第一个棕色牌位指去:“这个人!她生前一向理解你、她死后也一定会谅解你,可你!对得起她吗!”
黎墨向着唐晁手指的方向望去,这块灵牌,是在列所有灵牌中,最新的一个。
每年某个指定的日子,黎墨都会独自来到这里,对着这个牌位说上一整天的话。
他一直坚信自己的母亲就附身在这个牌位上,自己作为儿子所说的每一句话,唐柔都能够听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