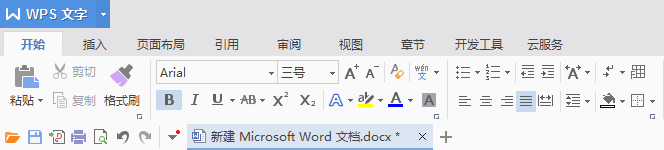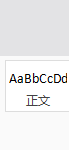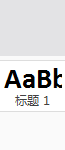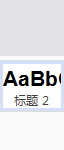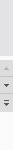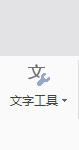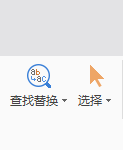任凭南乔声嘶力竭,喊破了喉咙,也无人应声,只有骆驼略显忧伤地望着南乔在那发狂。
直到南乔张大着嘴巴,却传不出任何声息之时,才算偃旗息鼓,绝望地瘫坐在昨晚他与水湄的栖息之处。没过多久,南乔似乎想起什么,挥舞着双手,开始挖掘身后的沙堆,眼瞅着沙丘被他扫荡成平地,也没见水湄的人影。
南乔彻底没辙了,原想着大哭一场,却忆起师父曾说,男儿有泪不轻弹,可如今却是到了伤心处,没等完成师父的重托,竟先把师妹给弄丢了,而且是在这茫茫大漠,若是找不回师妹,她定然是凶多吉少,哪怕她带走这两峰骆驼也是好的啊。
想到此处,南乔痛苦地闭上双眼,不敢再深想下去,随后便直起身来,憋足一口气,沿着宿营地,撒腿跑起来,绕了一个大圈回来,还是一无所获。
“一个大活人,总不能说没就没了吧?”南乔缓了口气,眼睛瞪着骆驼,自语着,又飞奔到骆驼身旁,用手使劲地拍打着它们俩,叫道,“你们倒是说句话啊,水湄到底去哪了?”
骆驼却目光温和地回望着南迁,嘴里反刍着草食,无动于衷。
潺潺流水声,又在南桥的耳际响起,他突然惊叫道:“莫非是昨夜那个墓中女子在作怪?”
刚刚看到了一缕希望的南乔,却又低垂下头,嘟囔道:“不对呀,她不是化成粉末了吗?”
有个骆驼却打了个响鼻,像是在鼓励南乔的推断,南乔抬眼与骆驼对望着,问道:“是不是有位女子劫走了我的师妹?”
不料,那骆驼竟回应了一声嘶鸣。
南乔心中大喜,赶忙牵起骆驼,抬腿就奔向了昨晚遇到的那条河流,边走边道:“找不到师妹,誓不罢休。”
等南乔涉过河去,凭着记忆,原路走回那座山丘之时,除却枯树林还在,静静地迎着阳光,然后便是黄沙漫野,哪有什么墓地可寻?
南乔顿时傻了眼,闭着眼睛回忆了好久,也没个所以然。随后,他找了根粗壮的枯木,将骆驼拴好,独自绕着山丘走了一遭,还是没有任何发现。
大漠风平浪静,身后河水荡漾,南乔竟生出恍若隔世的感觉,难道此行从开始就未曾发生过?或许师妹水湄还在师父膝前承欢?莫不是自己置身于梦境之中?
南乔将手臂探入骆驼口中,试图让它咬上一口,想看看此番是梦还是真?
骆驼异常地温顺,只是卷起舌头,舔了舔南乔咸滋滋地肌肤,并没张口去咬,还柔和地看了南乔几眼。
就在南乔失望地从骆驼嘴里抽出手掌之时,却不小心被它尖利的牙齿划了一下,南乔感觉到了疼痛,才猛然醒悟,哪来的什么梦幻,他真真切切地把师妹给弄丢了。
“师妹已然失踪,我也没脸回去见师父他老人家,为今之计,只能从长计议,咱们就在此处落脚吧,你们去岸边啃食青草,我思谋一下搜寻的策略。”南迁冲着骆驼念道,松开了它们的缰绳。
骆驼似乎听懂了南乔的絮语,慢吞吞地结伴临近河边,先是喝足了水,然后低着头,啃着肥美的水草。
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,南乔目送着夕阳西下,焦灼而燥热的一天结束了。骆驼们许是吃饱了肚子,卧在水边,嘴巴还在不停地嚼动着,双眸安详柔顺,静若处子,那副与世无争而又无忧无虑地神态,竟让南乔心生羡慕之情。
南乔望着驼背上装着干粮的包袱,却无心去取,也不觉腹中饥饿,眼前始终浮现着师妹的音容笑貌,心里便念叨着,湄儿不知吃饱肚子没,有没有水喝?她一个姑娘家,如何能捱过这荒漠日夜的酷热与寒冷?念及到此,南乔真是心如刀绞,五内俱焚,强忍着泪水,不让它喷涌而出。
搜肠刮肚,也没想出个好主意,南乔只好闭上眼睛,侧耳倾听,看看能否捕捉到师妹一丝一毫的讯息。
月色皎洁,河水澹澹,白日里那满目的黄沙此刻却被月光镀成灰白色,静谧地沉睡着,骆驼们喘气都是那般地悄无声息,生怕惊扰了大漠的梦境。
南乔心急似火,越是夜深,越是担忧着师妹的安危,他突然站起身来,扯着嗓子喊了几声水湄,嘶哑的声息朝向四周传递着,绵延而悠长,在空旷的大漠里显得格外高昂和激越。
南乔喊了几声,便摒住呼吸,仔细来听,还是没有师妹的回应。他痛楚地摇着头,眼泪在眼眶中打着转转,眼瞅着便要滴落下来,却突觉一股暗香袭来,扑向他的鼻孔。
南乔猛地回头去看那片枯树林,不由得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昨夜那片墓地竟再次出现在他的视野之内,众多坟墓环绕着中央的那座大墓,根根巨柱环伺其外,像是仰着头颅,迎着主宰万物的太阳。
南迁愣了愣神,以为看花眼了,先是闭上双目,定了定心神,然后才睁眼去瞧,竟真是昨夜所见的那堆坟茔,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,心道,难不成遇到了鬼打墙,为何白天却是一片寂静地黄沙,到了夜里,此处竟成了坟地,莫不是斗转星移?
问道之人倒是不怕妖魔鬼怪,南乔跟随着师父,早就练就了斩妖除魔之法,也学会了道家绝学天极之怒的招招式式,但事情太过诡异,不得不令他心存疑虑。
水湄的踪迹,毫无头绪,尽管南乔并不愿打扰墓地的清静,但想起昨夜与那诡谲女子的对话,也许这便是唯一的线索了。
南迁不再犹豫,毅然决然地走向那座中央大墓。待凑近去看,木棺竟恢复如初,棺盖紧致地与棺身合为一体,空气中暗香浮动,一切是那么的安详平静,似乎南乔从没涉足到此那般。
南乔的心中却是波涛汹涌,与眼前的气氛截然不同,能否找回师妹,只能开棺查看,希翼找到些蛛丝马迹,除此之外,已然是无计可施,黔驴技穷了。
南乔双手合十,朝着木棺拜了几拜,又念叨着:“在下寻找师妹心切,若是搅扰了尊驾的清梦,还请包涵。”
说完,便凑近木棺,双手搭在棺盖边缘,双臂较力,猛地一推,却是纹丝不动。
南乔自然不会服输,重新来过,反复几回,累得满头大汗,却无法撼动分毫,恍惚间听闻棺中传来银铃般笑声,像是嘲笑他过于笨拙,愈加令南乔羞愧难当,汗颜不已。
“不给你些厉害瞧瞧,还以为在下对你无可奈何呢?”南乔热血沸腾,向后退了几步,憋足力道,双腿蹬地,猛然向木棺冲去,就在双手与棺盖触及之际,谁料想,那棺上的盖子却自行移动开来,把南乔弄个措手不及,整个人扑入棺中。
南乔猝不及防地闯入木棺之内,只觉着身体之下很是柔软,连忙抬头来看,竟面对着昨夜那位女子的脸。
“对不住了,在下实属偶然为之,冲撞之处,莫要怪罪。”南乔赶紧从棺中爬了出来,嘴里道着歉意。
整理好衣衫,南乔这才再去端详着那棺中女子,毫无疑问,就是昨晚与他对话之人,模样确是与水湄有些相似,只不过多了几分媚气而已。
南乔不免有些纳闷,眼见着她已化为灰烬,如何却又全须全尾地躺在这棺材之中,莫非昨晚出现了幻觉不成?虽心存疑虑,此时的南乔也没心思再去计较,并没多问,双手抱拳,直奔主题:“在下失礼,请尊驾莫管,师妹走失,烦劳尊驾指点迷津,若能寻回水湄,在下自是感激不尽。”
那棺中女子像是睡意正浓,双眼微闭,略带一丝笑容,任凭南乔在那百般乞求,竟是一言不发,毫不理会。
无奈之下,南乔失望地将棺盖扶起,谁知费尽气力,那棺盖像是着了魔,盖上便滑落下去,连番几次,皆都如此,把南乔弄得满头大汗,也没能遂之所愿。
南乔瘫坐在棺木旁,叹息道:“莫怪在下愚笨,这物件竟邪了门,任凭在下用尽了力道,也无法给尊驾盖棺,请容在下不力之错。”
说罢,便要挣扎着起身走开,谁想他随意瞄了一眼,却发现棺盖上竟有字迹可寻,南乔用心来瞧,原来是刻着一首诗:此去东南千百步,邻水小院生桐树。峰回路转茅炊里,望断黄沙无去处。
南乔读罢,兴奋异常,连声道谢,随后又下意识去抬棺盖,却是轻轻松松地扶正盖紧,拜了几拜,这才转身离去。
回到骆驼身旁,南乔便想连夜动身,沿着河流,一路向东南而去。当他扯起缰绳,却发觉它们晃动着脖颈,并不愿随之起身,便也就作罢了,只好强压着心中的期颐,等待着天明。
席地打坐,微闭双目,南乔先是咏诵了一遍道德经文,又背诵了几遍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和《周易》三部道家经典,可还是毫无困意,便腾身而起,温习着天极之怒的一招一式,连续推出洞明、云开、风起、雷断、雾锁、电闪、水湮、火熔、天怒等一整套九式天极之怒。
练了几番,南乔一如既往地感觉到最后一式天怒还是那般地力不从心,按说招式精准到位,内力也随之运行于任督二脉,可为何就是不能融会贯通,气若长虹,总觉着体内有阻塞之感,无法抵达随心所欲的境界。
听师父曾提起,伏羲氏所创的天极之怒和天行剑法,乃为道家两门心法绝学,自古秘传至今,学得些许皮毛,便可叱咤江湖,横行寰宇,无人能出其右,可是集大成者却是寥寥无几,究其缘由,便是缺少了一种物件来开启根骨,使之日月贯通,水乳交融,万流归宗。
南乔有幸学得了天极之怒,而师妹水湄习得天行剑法,两人都遭遇了同样的梗阻,至今也无法得心应手,化腐朽为神奇。当问起师父,那物件是何种宝物之时,闻天道长却只回了“天机”两个字,而后表情有些古怪,再不多言。
临行之前,师父只是交代给他们俩,直奔位于罗布卓尔的楼兰古国遗址,寻到楼兰沙塔,若能应缘而开,其中奥妙便可尽知。也就这般寥寥几语,却是玄机难测,南乔也不知师父为何要让自己和师妹费尽周折,千辛万苦地赶到这荒漠之内,但冥冥之中,总觉着与那个物件相关。
既然突破不了天极之怒最后的那道关口,南乔索性收了招式,端坐调息起来,待心平气和之后,便有了睡意。
大漠之夜,万籁俱静,连几声蛙鸣都听不到,南乔渐渐地进入了梦乡,却似梦似幻地被一阵子香风所吸引,迷迷糊糊地走进了一处金碧辉煌地厅堂之内,竟是雕栏玉砌,锦帷缎幔,雍容雅致,古朴生香。室内正中摆放着一座琴台,台前焚着一炉清香,烟气缭绕,正是那股子味道。有一妙龄女子身着华丽彩衣,轻舞纤指,抚琴弄曲,身旁还立着位玉树临风,姿貌甚伟的年轻后生,锦衣玉裘,微垂着头,吹箫以和。
南乔见他们全神贯注,没敢相扰,屏声静气地听了一段,只觉着神清气爽,沁人心脾,琴箫稍止,便趋身打个稽首,问道:“此曲只应天上有,人间能得几回闻啊,恕在下冒昧,误闯宝地,不知两位所奏何种曲目?”
那女子缓缓地抬起头,眼眸平静地望着南乔,并无稍许的慌乱之色,似乎早就知道南乔莅临似的。
等南乔抬眼瞧去,那女子的样貌竟和棺中女子一模一样,便惊问道:“尊驾为何在此?”
“此曲早绝于世,乃为广陵止息也。”女子并未理会南乔的问询,只是淡淡地回应了一句曲目的名号。
南乔曾听师父提起过,广陵止息,又名广陵散,魏晋名士嵇康以擅弹此曲而著称,有一次,嵇康夜宿月华亭,夜不能寝,起坐抚琴,琴声优雅,打动一幽灵,那幽灵遂传《广陵散》于嵇康,更与嵇康约定:此曲不得教人。后来嵇康为司马昭所害,临死前,嵇康俱不伤感,唯叹惋:“袁孝尼尝请学此散,吾靳固不与,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!”
“阁下莫非便是那竹林七贤之嵇康前辈?”南乔思索片刻,将目光转向那个男子,问完这句话,竟有些呆愣起来。
那男子样貌与南乔太过相似了,说是孪生兄弟也不为过,若不是那身华贵衣履映衬得光彩照人,南乔还以为自己学会了分身术呐。
南乔没等那男子应声,抬手指着他问:“你,你是何人?”
那女子却莞尔一笑,替他回道:“他呀,号称九戒,是奴家的哥哥。”
“九戒,这名号倒是很有趣,世间都知晓有个随唐僧取经的八戒,你怎会多了一戒?”南乔瞅着眼前的男子,随口言道。
“多此一戒,便是将之前的八戒统统戒掉,省却了那些繁文缛节的臭规矩,老子就喜欢天马行空,自由自在,天地之间,寰宇之内,横行霸道,何人能敌?”眼瞅着那唤作九戒的男子温文儒雅,谁想到开口竟是这般粗犷豪爽。
南乔不想与他废话,又转脸问那女子:“多谢尊驾提点在下,不知尊驾名讳为何?”
“唤奴家沐新好了。”那女子浅笑一声,回道。
南乔恭恭敬敬地施个礼,谦恭地说道:“那就请沐新姑娘多言几句,告知在下师妹水湄是否安康?”
“棺内之诗,尽已言明,何必多此一问,不知你是痴愚,还是傻笨?”那个九戒却是不太耐烦,在旁吼叫了一声。
沐新笑吟吟地冲着哥哥劝道:“莫要吓坏了这位公子,既然登堂入室,便是贵客,要以礼相待,不要再对他吹胡子瞪眼了好吗?”
九戒白了白眼睛,手握玉箫,甩了几甩,别过脸去,不再搭理南乔,南乔却又问:“在下担忧师妹,还请沐新姑娘多多成全,莫要让她吃什么苦头才好。”
沐新并未作答,而是袅袅地站起身来,笑着问:“既来之,则安之,每个人自有定数,莫要再去思谋着你的师妹,咱们喝上几杯如何?”
南乔还想多打听些师妹的讯息,便未置可否,任由那沐新去里外张罗,自己便在琴台边,寻了个木凳,坐了下来。
琴台被沐新清理干净,便成了酒桌,几碟异域小菜随后便摆放齐整,三件质地精美的瓷碗分别置于他们三人面前。
九戒不知从何处拎出个酒坛子,不由分说地将南乔的酒碗斟满,南乔只觉异香扑鼻,便低头去看,竟是浓浓地血水,还泛着泡沫,顷刻间便吓得大惊失色,双股战栗,大汗淋漓,眼前一黑,从木凳上翻身落地。
等南乔醒来之时,却是漆黑一片,伸手不见五指。南乔试着用头往上顶了顶,竟有个盖子,覆在头顶。
南乔稍微用力,便将那盖子撞开,一缕月光透了进来。南乔直起腰身,再来瞧看,更是惊骇不已,自己竟置身在那座木棺之内,而那自称为沐新女子的尸身却不见了踪影。
http://client.hs.vread.com/album/detail.html?id=687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