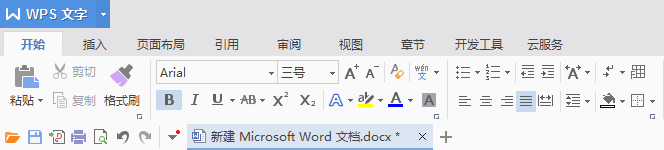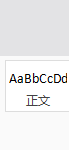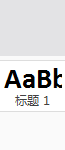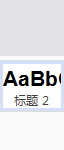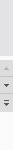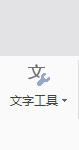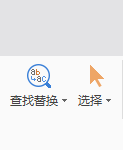鲁国倾尽举国之兵伐齐,导致国内空乏,秩序紊乱,鸡鸣狗盗之徒伺机而起。公子纠与柔姬乘车一路北去,为确保无虞,特意找来两身鲁军士兵的服制,分别换上, 而后御马如飞,匆匆向齐国驶去。
柔姬从未出过如此远门,长途奔袭颠得她十分头晕恶心。可柔姬顾念着公子纠急于赶路的心情,硬忍着没有做声。
为了转移注意力,柔姬试着与公子纠谈天:“公子怎如此熟稔曲阜到齐国这一路……”
公子纠头也不回,说道:“前阵子出过宫,一路行至洛阳,又经泰山回曲阜,故而很熟悉。”
柔姬点了点头,心头泛起几丝清苦:“公子上次出来,便是为了救公子小白和绿姬姑娘吧。”
公子纠紧紧盯着前方又长又曲折的小路,不置可否。
柔姬望着公子纠俊逸绝伦的侧颜,怅然道:“有日子没见过绿姬姑娘了,不知她是否还像从前那般貌美。”
公子纠想起绿姬,满心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,既有陈醋的酸涩又有醴酪的甘甜:“伊人如斯,是我变了。”
柔姬心弦一颤,尽量放缓声调,却仍是嗓音干涩:“公子是人变了,还是心变了……”
公子纠沉默了半晌,幽幽道:“若是能变心,又如何会如此痛苦。”
眼前的秋色霎时没了生气,柔姬红了眼眶,望着公子纠深邃的眼眸,无奈又无可奈何。他所说的,正是此时自己的心境,造化弄人,他求而不得,她求他不得,都是一样的心碎,却无法同病相怜。
突然间,数百名鲁军士兵从北向南一路逃命而来,丢盔卸甲,如丧家之犬,又横冲直闯,似没头苍蝇。
公子纠忙将马车停在道旁,为他们让开去路。柔姬吓得蜷缩在公子纠身后,大气也不敢喘。公子纠面色平静,眸中却起了波澜,显然,眼下的情形颇为出乎他的意料。
待那一众鲁军撤退后,柔姬悄声问公子纠:“怎么会有如此多的逃兵?”
公子纠牵过缰绳,将马车驻在道旁的树丛里,对柔姬道:“我去问问……”
柔姬一把拉住公子纠的衣袖,公子纠一怔,略回过头,蹙着眉,似乎颇为不悦。柔姬赶忙缩了手,怯怯道:“公子别去,太危险了。”
公子纠不以为意:“既有如此多的逃兵,想来是小白胜了,我去探一探,你就在这里……”
远处忽传来阵阵马蹄声,有节律的渐渐逼近,公子纠忙收了声,拉着柔姬团身躲入了树丛中。
公子纠细细观察,只见踏马而来的,是一支相对齐整的军队,只是衣衫褴褛,看不出究竟是齐军还是鲁军。
道旁突然蹿出了几名残兵,生生截停了这支队伍,为首的像是受了极大的惊吓,险些从马上跌落。公子纠这才看清,为首那赤着上身发丝凌乱的,竟然是鲁国公。
鲁国公简直要被这几名鲁军士兵吓出了病,脸色苍白差点厥过去,见来人是鲁军士兵,鲁国公气得挥着马鞭,大骂道:“一群混蛋,好端端的突然蹿出来,想吓死寡人不成!”
士兵看到鲁国公的狼狈样,登时傻了眼,待回过神后,忙招招手,命同伴将被俘管仲带上前来,谄媚道:“君上勿怪,君上且看,我们抓到了管大夫……”
鲁国公看到管仲,气得鼻孔冒烟:“哼!什么管大夫,把这骗子即刻给寡人抓起来,寡人定要将他五马分尸!”
公子纠看到被缚的管仲,面色一沉,即刻要赶过去。柔姬死命拉住公子纠,低声劝道:“公子且再看看情势再说……”
公子纠想挣脱柔姬,力道轻了脱不开,力道重了又怕伤到她,只得耐着性子劝:“还有什么好看的,兵败如山倒,以你兄长的性情,定然要拿我师父撒气。”
柔姬仍不肯撒手:“公子既知如此,你去又有何裨益?鲁国兵败,管大夫难辞其咎,就算我兄长责罚他,亦在情理之中啊。”
公子纠听了这话,再难动心忍性,也顾不上伤不伤柔姬了,一把将她推开,欲大步上前。
柔姬被推倒在地,却顾不上周身吃痛,跑上前去,一面拦住公子纠的去路,一面拔出腰间的短刀,满面倔强。
公子纠冷眼望着柔姬:“姑娘这是何意?”
柔姬将短刀往脖颈间一横,语气虽柔顺却异常坚定:“公子快挟持我。”
公子纠一怔,站着没动。
柔姬用眼角余光扫见鲁国公已将刀架到了管仲脖子上,跺着脚急道:“公子,切莫再犹豫了!”
公子纠见状,再不顾忌,一把拉过柔姬,接过刀柄,挟着她大步向鲁国公处走去。
鲁国公正气急败坏,看到翩翩而来的公子纠和被挟持的柔姬,一下傻了眼。
公子纠神色淡漠,冷道:“放了我师父,我就放了你们女公子。”
比鲁国公更加震惊的是管仲,管仲未曾想,公子纠竟然自己从鲁国宫中跑了出来。可他既然已脱险,为何还要凑上来?管仲被粗麻绳勒口,嘴角尽是鲜血,仍卯足了劲断断续续含含糊糊道:“公…公子,快……走……”
公子纠见管仲被如此对待,面色异常难看,语调里尽是愠恼:“放了我师父!”
鲁国公冷笑几声,阴阳怪气道:“二舅父真是重情重义。管大夫将你的性命押给了寡人,你非但不怨恨,还要救他!寡人举全国之兵,助你夺位,如今损兵折将,你们师徒二人难逃其咎!今日我倒要看看,一向磊落坦荡的二舅父,是否会为你师父,而残杀无辜的女子。来人!把公子纠也给我抓起来!”
话音方落,数名戎装士兵冲上前来,将公子纠团团围住。公子纠见状,将柔姬挡在身后,挥刀只身与之对抗。
士兵举长刀劈头盖脸砍下,公子纠以一柄短刀抵挡,不使蛮力只以巧劲相抗,加之身姿轻盈步伐灵活,几回合下来,竟未居下风。
柔姬却吓得惊叫连连,苦求道:“兄长,公子一直不主战,也未曾参与排兵布阵,兄长就算有气,看着柔儿的面,就别怪罪公子了……”
忽有报探快速御马上前,满头大汗,气喘吁吁对鲁国公道:“君上,快逃吧,齐国公率兵追过来了,离此地已不足十里!”
鲁国公吓得魂飞魄散,结结巴巴下令道:“快,快快!快撤!”
可公子纠仍在乱阵中以寡敌众,场面僵持不下,难解难分。鲁国公见状,翻身下马,拉过自己的大弓来到阵前,弯弓瞄准了公子纠。
裨将在一旁劝阻道:“君上!不可,若是误伤了女公子……”
鲁国公狞笑一声,将箭锋一偏,直冲着柔姬射了过去。
这是一场阴谋与人性的赌博,输赢只在一瞬间。果然,公子纠见箭矢冲着柔姬飞去,赶忙一团身,拉着她躲开了箭矢。
趁此机会,公子纠后身放空,众士兵一拥而上,合力擒住了公子纠。
鲁国公大笑几声,怒道:“把公子纠和管仲师徒捆起来押下去!等回宫后,即刻将他们五马分尸!”
柔姬见公子纠被俘,急得直掉眼泪。柔姬捡起公子纠丢掉的刀柄,横在脖颈间,挡在高头大马前,哭道:“兄长不允诺放过公子,柔儿就先公子一步去了!”
鲁国公本就暴怒不已,此刻见柔姬以死相逼,不由气急败坏,七窍生烟。
方才为鲁国公断后抵挡齐军先锋的公子友率部上前,虽不知前因后果,但看到公子纠与管仲被俘,柔姬又以死相逼,便猜出了个大概。公子友权衡了片刻,打马上前,拱手劝道:“君上,齐国三军会合,齐国公亲率数万兵马,已逼近此地。留公子纠与管仲师徒在此,对齐国公也是个威慑,何必此时赶尽杀绝,筹码尽失……”
齐军的前锋已渐渐逼近,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。鲁国公回头望见地平线尽头黑压压赶来的数万齐军,吓得浑身哆嗦,急急打马,招呼着身后众人:“不杀了不杀了,快撤!快跟上!”
可柔姬仍戳着没动,公子友忙下马,上前规劝了柔姬几句,柔姬明白事情紧急,虽万般不情愿,仍乖乖上了一辆马车。
公子纠与管仲师徒被押上另一辆马车,眼见就要落入齐军的射程,鲁军众将如丧家之犬,豁出命奋力打马,快速向曲阜逃去。
马车上,管仲与公子纠被绑得结结实实,由两名鲁军士兵看管着。
管仲面色如铁,一副悔不当初的样子;公子纠却面色淡然,一如往常。
小白亲驾战车,率领齐军越追越近,看管两人的士兵不得不从马车窗中探出身,以弩狙击齐国的追兵。
小白眼尖看到前面秃发赤身的鲁国公,实在忍不住笑,连执鞭的手都疲软了几分。
但他不想错失良机,忙收敛了情绪,抽出身后的铜剑,双脚登上车衡,纵身一跃跳上了马,挥刀斩断皮绳,将笨重的战车舍弃,快速御马向鲁国公追去。
鲁军这支残兵败将,看到小白追了上来,吓得魂飞魄散,纷纷回身弯弓搭箭,射向小白。
小白匍匐在马背上,将铜剑舞得密不透风,利索地挡掉了全部的箭矢。趁众人再抽箭的功夫,小白以极快地速度拉弓,只听得“嗖嗖”几声,队尾战车上的两名鲁军士兵被射中,未及挣扎,就一命呜呼。
周围的士兵一边高喊“保护君上”,一边加快了打马的速度。
著山与那几名少年御马赶了上来,抵挡在小白左右,以保护他的安全。
曲阜城近在眼前,小白不能再等,找准时机从后侧方绕过鲁军的队伍,大力弯弓射向了鲁国公。
公子友不顾一己之身,用弓为鲁国公挡开了小白的箭,自己却险些坠马。
曲阜城城门大开,鲁国公快马加鞭赶进了城。小白见鲁国公进城了,以自己与著山数人之力,决不能盲目追进去,忙举剑示意驻跸。
待公子友、柔姬、管仲和纠所乘的车马皆进了城,鲁国公不顾队尾的诸多鲁国士兵,吩咐守门的侍卫,立即关城门。
守门的侍卫见自己的国君赤身披发,慌不择路,不敢怠慢,顾不得城外的同伴,重重叩上了城门。
鲁国公进了曲阜城,仍吓得浑身哆嗦:“四面城门紧闭,命弓箭手登城,有靠近城墙者,格杀勿论!”
公子友赶忙劝阻:“君上,不可!我军已损兵折将,若是再自相残杀,天理难容!”
鲁国公回道:“若有齐军的奸细混进城,里应外合,你能奈何?速速回宫,召集群臣商议对策!”
小白与著山返回城外十里,与国高两大夫所率的其他军队会合。著山下马后,跪地揖道:“属下无能,未能活捉鲁国公,请君上降罪!”
小白也下了马,扶着著山,说道:“鲁国公奸猾无常,你已经做得很好了,不必请罪。”
著山却仍不肯起身,满面懊悔:“战前君上说,让我凭本事回到你身边,这次是没机会了。”
鲍叔牙走下马车,捋着胡子,笑着上前:“小崽子,谁说没有机会了?”
小白会心一笑,朗声对著山道:“传寡人令,高氏右军下士著山,身先士卒,驱逐鲁军,于国有功,特命调回我中军帐下,为虎贲氏!”
著山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,待反应过来时,忙拜道:“谢君上!”
鲍叔牙上前拍了拍著山的肩,嘱咐道:“小崽子,诸事多上心!”
著山无比欢悦地应了一声,而后退到了一旁。
高氏大夫上前,对小白道:“君上,方才斥候来报,管夷吾已被鲁军抓获,现与公子纠一道在曲阜城中。君上如何打算,是否要继续攻打曲阜。”
小白沉吟片刻,问道:“诸位大夫以为,鲁公会如何对待我兄长。”
国氏与高氏仍在思忖,鲍叔牙便抢先道:“鲁军大败而归,国中必有怨者。我担心,如若将鲁公逼得太急,会对公子纠不利。”
小白觑眼望着鲍叔牙,揶揄道:“此役乃是由管夷吾指挥,兵败之责,全在于他,与我兄长何干。师父怕是担心鲁国公会对管夷吾不利吧?”
见小白一下子看穿了自己的想法,鲍叔牙竟然脸色涨红,辩解道:“胡说!为师乃是为君上和齐国筹谋。如今鲁军已有城池之固,而我军又深入敌境,贸然攻之,并非上策。”
高氏大夫拱手道:“且不说鲁国公究竟会怪罪于谁,姒大夫所言在理。”
国氏大夫附议道:“臣亦深以为然。”
小白点了点头,却不置可否,只是满面肃然地望着不远处的曲阜城,眸中寒光四溢。
鲍叔牙摸不清小白心中究竟如何打算,甚是忧虑。
与此同时,鲁宫正殿里,鲁国公终于穿好了衣衫,梳拢了被割得七零八乱的发丝,坐在大殿正中,一副君临天下的模样。
可他额角上渗出的细汗仍暴露了他内心的慌张凌乱,鲁国公色厉内荏,板着脸问堂下诸臣:“现在齐军离曲阜只有不到二十里,众卿可有退敌良策?”
堂中诸人鸦雀无声,低垂着头,大气也不敢出。数日前,出兵之时,谁能想到,鲁国十万大军竟会被齐军三万余人打得落花流水,惨败而还?现下这群文臣武将都未回过神来,哪里还有心力去想,如何冲破齐军的阵。
鲁国公见众臣都不说话,气得七窍生烟:“好啊,你们一个个都缩着头,不敢应承,寡人养你们何用?不如即刻就把你们扔出曲阜城去!”
众臣见鲁国公大怒,忙俯身叩首请罪:“臣等知罪!”
鲁国公更气了:“知罪有什么用?你们倒是想办法啊!”
一发须尽白的老臣碎步上前,拜道:“君上,以老臣之见,齐国公此次率军前来,主要是想要个说法。君上只需将这一战的罪责全部推在管仲与公子纠师徒身上,将他二人杀掉,给齐国公一个交代便是了。”
鲁国公想了想,蹙眉问道:“是吗?可寡人听闻二舅父与小舅父兄弟情深,上次在咱们宫里,二舅父也曾为保护小舅父,曾以命相搏,会不会……”
另一位大臣上前拜道:“君上,臣附议,公子纠与齐国公不仅有君位纷争,传言还牵扯一段情感纠纷,由此看,只怕两人关系不会有多好。更何况,公子纠存在一日,便会威胁齐国君位一日,可齐国公自己不便动手。如若君上能替他除掉公子纠,只怕齐国公会从心底感激。”
鲁国公想了想,转问站在前排的公子庆父:“咱们也是兄弟,你觉得呢?他们说的有道理吗?”
鲁国公这话问的奇怪,公子庆父不知该如何回答,只能说:“打仗磕到了头,现下想不清楚,君上拿主意就是了。”
鲁国公呆坐在原地,蹙眉思索着,无比犹豫,不知究竟该如何处置管仲与公子纠两人。
姝子苑内,绿姬坐在秋千架上,心神不宁地荡着秋千。
隆冬将至,狐裘不暖,哪怕太阳当头,霜雾也弥久不散。猜测小白应当率军到了曲阜,绿姬的心不由地提到了嗓子眼,无比紧张,满手都是汗。
人人皆以为齐军打败鲁军,便代表此战的胜利,可在绿姬心中,只有知道小白与公子纠皆平安无事,六煞得解,才可以彻底放下心来。
懒丫头端了杯温水,从内室而来,看到绿姬惴惴不安的样子,懒丫头万分不解:“姑娘怎么了?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。”
绿姬不想让懒丫头担心,强笑几下,说道:“没事,前几日操心太过,或许是太累了。”
懒丫头将水递给了绿姬,问道:“姑娘,我一直不明白,姑娘身为大卜一脉,掐算天命,怎会算不出此战的胜败?”
绿姬笑回道:“天道可循,万物有序,唯有人心难预测,战争乃是人祸,如何能掐算得出?”
懒丫头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:“反正只要我们公子和我哥哥无事便好了,别的我也管不了那么许多。”
绿姬没再接话,思绪回到那日在泰山中,与公子纠话别,她问公子纠,如若管仲战胜,是否会杀小白。公子纠未正面回答,却笑得如沐春风:“小白的答案,便是我的答案。”
绿姬轻摇摇头,不愿再去想。六煞命格再难解,也总比人心好预测,绿姬幽幽叹了口气,站起身,戳在梨树下发呆。
只是她不知道,就在她担忧公子纠生死的时候,一骑绝尘从洛阳而来,带着密报,驶入了齐国宫中。
周天子未允婚,小白却下定了决心要娶绿姬为妻。这情报落在有心人的眼中,势必又会掀起一场风雨。
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只是曲阜城外的小白和姝子苑中的绿姬,都在担忧着公子纠的生死,却丝毫不知山雨欲来,而他们已站在了暴风眼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