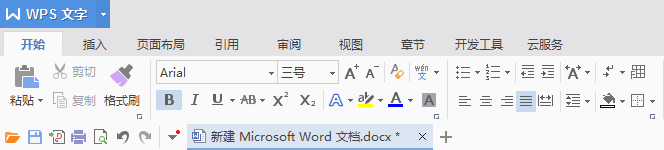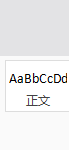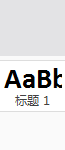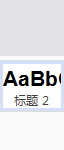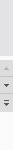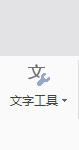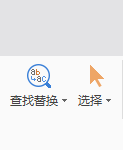缺月挂疏桐,更深霜露浓。
时至深秋,天寒雾冻。姝子苑暖阁内,青铜火盆烧得正旺,卧榻上早已添了羊皮毛被,借以抵御寒潮。
虽然舒适宜人,绿姬却毫无睡意,在榻上辗转反侧,难以入眠。
眼见要打仗了,绿姬实在忐忑不安。毕竟在这场战争中,双方力量悬殊,龙战鱼骇,又有卫国与莒国涉入,形势复杂,瞬息万变。即便身为大卜一脉后人,绿姬也难以洞悉时局。
更何况,小白与公子纠又是相生相克的命格。小白已为公子纠解了五煞,可孰能想到,独剩下这一煞,竟是如此的危险,如涉龙潭虎穴,九死一生。
绿姬从榻上起身,披上绢缎深衣,走到窗边,望着清冷的月色出神。
苑中梨树下,小白正坐在石案旁,对着一张皱巴巴的羊皮卷地图,看得极其认真。
案上的油灯随着夜风时灭时明,小白却丝毫未察觉,晶亮的眼眸星光闪耀,直比天上的星子更夺目。
绿姬无奈一笑,拉紧衣袍,起身出了暖阁。
小白听到拉门响动,抬起眼,看到站在树影下清丽如仙的绿姬,嘴角泛起一抹调笑:“这么晚了,不好好休息,竟藏在树影里偷偷看我。”
绿姬轻哼一声,慢步上前:“白日里就见你和姒大夫对着地图嘀嘀咕咕,晚上竟还不休息。你只说,这几日,你可有睡足两个时辰?”
小白笑而不答,大手紧紧握住绿姬的小手:“既然不想睡,就陪我坐会儿吧。”
绿姬看了看足下的青石板地,只觉一阵大寒,她瞥了小白一眼,嗔道:“唯有一个蒲团子,你自己坐了,还让我坐哪去?”
小白俊眉一挑,拍了拍自己的大腿股:“坐我身上啊。”
绿姬陡然将手从小白的大手中抽出,转身回了暖阁。不一会儿,她拿着个蒲团子又走了出来,放在小白身侧,俯身跪下坐好。
小白看绿姬衣衫单薄,不禁颇为心疼:“穿这样少,可别冻坏了身子。”
绿姬的侧颜在月色下美得惊人,她红着小脸儿,钻进小白怀中,呢喃道:“这样就不冷了。”
小白的俊脸上满是掩不住的笑意,怀中这瘦弱的小人儿像是一簇小小的火苗,燃尽了他心头的全部烦忧,炸开了如星吹雨般的烟火。
小白忽然起了玩心,微扬起下巴,蹭着绿姬光洁的面颊:“既然不想睡,不如我们便就着这地图,推演一盘?”
白日里听小白和鲍叔牙商讨兵法,绿姬虽听出了些眉目,却并无自信:“我只是略略听懂怎么推演,谋略却一点都比不上你师父和管仲。”
小白笑道:“切莫自谦,夫人冰雪聪明,甚至超过我那几个军师,此时不帮你夫君,更待何时呢?”
绿姬没办法,只得应道:“就一盘,推演完便去睡,不然照你这个熬法,铜铸的身子也受不了,还未等到两军对垒,自己便要先病了。”
小白见绿姬答应了,满怀欣喜地把地图上赤色的琥珀石子和蓝色的绿松石子归位:“夫人且看,这石子上有的刻的有字,有的无字。有字的,便是由将军或大夫率领的主力军。比如这石子上刻着‘高’的,便是高氏大夫的军队,鲁国这边也一样。所以,夫人是要当齐军还是当鲁军?”
绿姬眨眨清眸,说道:“自然是齐军,谁要扮那寡廉鲜耻的鲁国公的军队。”
小白抬手刮了下绿姬尖翘的鼻尖,赞道:“好,有志气!只是如此便莫怪我倚强凌弱了。”说着,小白将代表鲁军的绿松石子从曲阜移出,沿着地图上的路线向东推进,边移边解释,“齐国与鲁国以泰山相隔,与燕地以河川相隔,东有莒国,西有卫国。如今齐莒联盟,管仲必不会借道莒国,而一定会向西,沿济水东岸绕过泰山,来攻打齐国。”
绿姬将琥珀石子有字的一面扣向下,挑拣了四个,移至临淄西面的泺邑。
小白见状,不敢贸然用主力攻城,只移出一个绿松石子试探,绿姬遂将城中的一枚琥珀石翻过来,只见上面用金文刻了个“鲍”字。
小白微微一笑:“好啊,把国高两军和我师父的军队都调出来,以主力屯兵泺邑,正面拦截鲁国军队?这招我倒是没想过。”
绿姬歪着小脑袋,一字一顿道:“这招叫当门棒狗,专打不请自来的坏人。”
小白笑道:“行,既然这样,我不打你。”小白推着绿松石子绕过泺邑,继续向东,到时水之畔,一举越过了时水。
绿姬急了,忙按住小白的手:“你耍赖,这有条河。”
小白一笑,揽着绿姬的肩,说道:“夫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,此地名为乾时,雨水丰沛之时大军难以渡河,可今年是旱年,乾时多浅滩,所以我可以从此过河。”
绿姬想了想,黑水银般晶亮的眸子一转:“那是你以为”,说着,绿姬拿出一颗琥珀石摆在时水上游,玩笑道,“如此,这河里便又有水了。”
小白看着绿姬,满面宠溺:“好,我就算你发了大水便是”,说着,小白收起七颗绿松石中的四颗,还剩三颗,渡过河岸,“如此,临淄空虚,夫人的主力军队恐怕来不及撤回了。”
绿姬不慌不忙地拿出仅剩的两颗石子,摆放在河岸两侧。
小白不以为然:“你的主力都放在泺邑了,其余皆没什么战斗力,埋伏在此又有何用”,说着,小白伸手去翻那两颗琥珀石,却意外发现,石子上竟刻着“国”、“高”两个金文。
小白愕然,立即翻开绿姬摆在泺邑城中的另外两颗石子,只见石子上是空白的,并无铭文,表明这一支队伍不过是名不见经传的小兵。
方才小白见绿姬从临淄城中派出大军,其中一支为鲍叔牙的队伍,便想当然地以为她派出的是齐军主力。谁知她竟是虚张声势,以鲍叔牙的军队为饵,迷惑敌人。
绿姬笑道:“这便叫关门打狗。我国高两军虎狼之师,在此地以逸待劳,专打你这被河水冲击后,丢盔卸甲的残兵败将。这一盘,我赢了,你可别耍赖,还不快去睡觉。”
绿姬话音才落,突有顿悟,忙抬眼看着小白。小白也瞪大了星眸,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绿姬。
猛然间,小白一把将绿姬拉进怀中,无比兴奋地嚷道:“夫人真是上天派来助我的福星!”
翌日清晨,鲍叔牙和隰朋早早进了宫。
守宫门的侍卫看见鲍叔牙和隰朋,恭敬礼道:“姒大夫,隰大夫,两位直接去正殿即可,君上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。”
鲍叔牙和隰朋闻言,交换了神色,不敢怠慢,三步并做两步,向正殿赶去。
走到正殿前,守在一旁的侍卫赶忙拉开扉门。鲍叔牙与隰朋走进正殿,方要跪地行礼,歪躺在席上的小白立刻直起了身子,摆手制止:“师父,隰大夫,不必拘礼,随便坐吧,我这里有几件要紧事,要请你们去做。”
鲍叔牙喘了口气,在隰朋的搀扶下缓缓坐下:“君上可是有了鲁军的动向。”
小白满面自得:“非也,只是与齐鲁之战有关”,说着,小白将羊皮地图摊开铺好,问道,“师父可懂治水之术?”
没想到小白会问这么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,鲍叔牙着实摸不着头脑。可看小白神色,不像是在玩笑,鲍叔牙回道:“古之治水之道,《禹贡》中曾有记载,为师略通一二。”
小白如释重负:“如此甚好。这第一件事,便是勘察临淄以西各路河川的水情,再带掌管工事的冬官前去,依据实际情况,分段拦筑堤坝,要能控制好上、中、下游每一段的水流,做到不旱不涝,不涸不淹。”
鲍叔牙想了想,回道:“今年齐国大旱,诸川水流平缓,君上这要求应该不难。只是大战在即,君上为何此时关心起治水了?”
小白神秘一笑:“师父不必多问,到时候自然就知道了。我唯一担心的,便是师父的身体。师父到底上了年纪,这劳心费力的事请你去做。万一操心过度,脱发秃揭了,或是劳力伤神,崴脚摔瘸了,可如何了得。”
小白对鲍叔牙的孝顺之意,发自真心。可鲍叔牙听了这话,却气得直咳嗽。隰朋忙抚着鲍叔牙的背,为他顺气:“姒大夫腿脚不便,不宜出远门。不如由朋代大夫前去,朋略懂工事,可张罗完成筑堤之事。”
小白想了想,点点头:“没错,师父上了年纪,总去那河滩里走,容易崴脚。隰大夫乃是我齐国上大夫公孙戴仲之子,又是师父看重的贤才,由你去督办,师父和我都可以安心。”
鲍叔牙沉默半晌,苦笑道:“果真是不中用了,竟像废人一样,需要大家照顾着。这是其一,其二呢?”
小白凑上前薅着鲍叔牙的胡子,安抚道:“师父可别多想了,让你此时节省心力,则是有更重要的事等师父去做。再说说这第二件事,便是火速为国氏和高氏各赶制一千面军旗,一千面战鼓。”
鲍叔牙满面狐疑:“君上,国氏和高氏军中并不缺军旗和战鼓,为何……”
小白一脸贼笑,依旧不肯言明:“师父不必问,只管按我说的去做便是。”
既然小白不愿多说,鲍叔牙也懒得再追问:“君上还有什么吩咐,一并说了罢。”
小白敛了笑容,正色道:“这第三件事,就是方才所说的,须得师父亲自去做,我才放心。”
秋阳升上枝头,农闲的庄稼汉们才从睡梦中醒来,三军中的将士们却已完成了晨起的训练。
将士们三五成群,结伴回营,准备用早饭,才到营地门口,就看到一个清瘦弱小的身影,孤零零地站在营门外。
懒丫头看到这么多身穿战服短褐的士兵,吓得手足无措,搓着衣角直往篱笆墙后躲。
著山在人群里冷眼看着懒丫头,听着周围的人议论她是谁家的妹妹或是相好的姑娘,冷哼了一声,视若无睹地转身向营帐大门走去。
懒丫头这才看到人群中的著山,顾不上害羞难堪,红着脸跑上去,拉住他的衣摆,唤道:“著山……”
其他兵士看到这模样可爱的小姑娘是来找著山的,都卯足了劲儿嗷嗷起哄。
著山却不领情,一把将衣摆从懒丫头手中拽出来,黑着脸,语气傲慢:“你不是又聋又哑不理人吗?还来找我做什么?”
其他人见气氛不大对,不敢再看热闹,三三两两互相推搡着,快步走回大营。
著山见懒丫头垂着头不答话,抬腿欲走。懒丫头赶忙跑上前,直直拦住了著山的去路。
著山一脸不耐烦:“找你你不理,现在又来我军营里闹,你到底想干什么?”
懒丫头涨红了小脸,磕磕巴巴:“有…有事找你帮忙。”
著山上前半步,站在懒丫头身前,俯视着眼前这小人儿:“没想到你是这种人,无事便对人不理不睬,有求就过来摇尾乞怜。”
著山去了军营后,长高了半头,身子黝黑紧实,已成了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懒丫头紧张得说不出话,断断续续道:“不,才不是……只是我听说,你要随君上去打仗了,若是遇上我们公子……”
著山昂着头,一脸顾全大局的样子:“这你不必操心,我们君上从未想要杀你们公子,若非你家大夫挑事,眼下这一战或可避免。”
懒丫头咬着薄唇:“我知道君上不会杀公子,可战场上太危险了,我想拜托你,若是你们交兵了,不要杀公子的侍卫大兴可以吗……”
著山没想到,懒丫头竟然是担心公子纠那侍卫,特来求自己照顾他。著山莫名十分生气,怒道:“不杀?他身为齐国人,却来杀齐人,此为叛国,罪无可恕!千万别让我遇见他,一旦遇见,我定要将他碎尸万段!”
听了著山这话,懒丫头急得直掉眼泪:“不行不行,不能杀他!”
懒丫头越哭,著山就越气,一把将面前的小人儿推开,著山撂下一句:“哭吧,你多哭一声,我就多捅他一刀”,扬长而去。
嘴上虽讨了便宜,苍白的面色却暴露了著山心底的愤怒。原来她不理他,不愿与他说话,皆是因为她心中惦记着旁人,著山心乱如麻,加快了离去的脚步,忽听得懒丫头在身后哭着喊道:“他是我兄长……”
著山一愣,回过身来,满面难以置信,他快步走回懒丫头面前,问道:“你说大兴是你兄长,可他不是犬戎人吗?听说管大夫从市上把他买来,他可是无父无母的。”
懒丫头抽泣着,回道:“大兴是我亲兄,因为全族被灭门,公子不想让他知道实情,就隐瞒了我们的兄妹关系……没空跟你详细解释了,我求,求求你……齐国的军队太厉害了,求求你,千万不要杀我兄长……”
懒丫头年岁尚小,对齐国军队的印象还一直停留在齐襄公在位时,攻无不克的样子,故而十分担心,自己兄长会在战乱中被杀。
著山心疼懒丫头身世,安抚道:“即便他不知道你是他妹妹,这世上你好赖还有个亲人。我却一个亲人都没有,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,是什么族人,只有君上和姒大夫,像我的亲人一样……你放心吧,若我能遇见你兄长,一定保护他,让他好好活着。”
懒丫头抬起小脸,晶莹的泪滴从大眼睛中滚落,楚楚动人:“真的吗……”
著山抬起手,笨拙地为懒丫头拭去泪珠:“大丈夫一言九鼎,决不食言。”
懒丫头这才破涕为笑,抓着著山的衣袖连蹦带跳:“著山你真好!”
著山一脸嫌弃,嘴角却不住上扬:“又哭又笑一脸鼻涕,真是恶心。”
懒丫头小嘴一撅,拿起手中的袖笼,直接擦了鼻涕。著山忙将衣袖拽回,惊怒交加:“我一会儿还要训练的,你……”
懒丫头咯咯地笑了起来,从内兜中摸出一个荷包,递给了著山:“这是我专门给你绣的,你拿着吧……”
著山接过荷包,看了看,眉头拧成了疙瘩:“绣的什么啊这么丑。”
懒丫头回道:“绿姬姑娘教我绣的,起初说是要绣鸳鸯,但我绣不好两只鸟,就只能绣一只,也许,是个水鸭吧。”
著山满面嫌弃:“你竟然绣了个鸭子给我。”
懒丫头红着小脸跺着脚:“反正你拿着吧,能保平安的。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啊,我等你”,话音未落,懒丫头便逃也似的跑了。
著山望着懒丫头的背影,无奈地摇了摇头,捏荷包的手却一丝也不放松,将它牢牢收在了贴身的内兜里。
莒城内的齐军营地,车马往来异常频繁。只见齐国的马车满载着装运粮草盔甲的布袋,一辆接着一辆驶入军营。莒国士兵们在齐国将军的率领下,不停操戈互击,练习劈刺之术。
北门城楼上,鲍叔牙与莒国公看着源源不断驶来的车马,喜形于色。莒国公冲鲍叔牙一揖:“请大夫替寡人向齐国公致谢,谢他信守诺言,派兵支援,实乃我莒国百姓之福。”
鲍叔牙笑着向莒公回礼:“莒国公与我们君上相识于微,为我们师徒一行遮风避雨,若非国公义举,又如何会有今日的君上。此等情谊,即便海枯石烂也不能忘怀。如今鲁国大举犯齐,又得国君倾力相助,我们怎还能受得起国公这个‘谢’字。”
莒国公摆摆手,略侧过身,不受鲍叔牙这一礼:“寡人国弱,背靠数位强邻,屡屡受人胁迫。只有齐国公诚意相交,寡人焉能不以诚相待?”
不远处,一商人模样的男子佯装方便,藏在草丛中,竖耳偷听,四下张望。半晌后,此人跨上马,朝鲁国的方向飞奔而去。
鲍叔牙捋着胡子,斜眼望着那一骑绝尘,笑意盈盈。
原来,这一切皆是鲍叔牙和莒国公故意做给那奸细看的。所谓的源源不断的齐军,不过是协防莒国的千名士兵,他们打北门入,从东门出,来回变换着不同的服装、旗帜和队形,从晨起开始已经走了三五趟。在不明真相的人眼中,就像有万人大军一般。
一旦莒国驻有齐国重兵,便相当于在鲁国背后藏了一把锋利的匕首,待鲁国大举伐齐,国内空虚,这部分兵力便可以打西侧绕过泰山,直捣曲阜,威胁鲁国的生死存亡。
泰山之巅,云破日出,东方破晓。
数百里外的鲁国宫内,公子纠从宿醉中苏醒,只觉四肢沉重,头痛欲裂。公子纠一惊,似是想起了什么,赶忙下了榻,向卧房外跑去。
小院内空空如也,一个人也没有,公子纠心中大叫不好,跨步走向门口,打开院门,只见两侍卫正把守着大门,披坚执锐,神色肃穆。
见公子纠打开门,两侍卫异常紧张,直直用身子挡住大门,稽首抱拳,示意公子纠不能出来。
公子纠目光凌厉如剑,却只能甩袖转身退了回来。昨晚管仲忽然找他对饮,说是他们师徒许久都未好好说话了,现下看来,不过是管仲欲灌醉他的套路。
他早就该想到,管仲怎会让他上前线,鲁公又怎会毫无牵制措施,就将十万大军拱手交出,任由管仲指挥。
公子纠原本以为,他能在沙场上略尽绵力,拼命护得小白周全,如今看来,却只能被关在这一方小小的院子里,焦灼煎熬地等待消息。
管仲是个守信之人,公子纠依稀记得昨晚酒席上,他曾让管仲保证,无论胜败,都不能杀小白,可管仲究竟答允了没有,公子纠竟然一点印象都没有了。
公子纠坐立不安,在小院中来回踱步。打翻侍卫逃出宫去简直是痴人说梦,还未到前线,就会被人追回来。更何况,现下情况究竟如何,鲁军是已经拔营杀向了齐国,还是刚刚集结,公子纠一无所知。
正一筹莫展之际,院门豁然大开,公子纠抬起头,看到来人是柔姬,又垂下头,像没看见似的,继续想自己的事情。
看到公子纠的态度,柔姬毫不意外,她淡然一笑,碎步上前,轻声对公子纠道:“公子,现下,只有我能帮你……”
东方已露鱼肚白,姝子苑小白房内依旧灯火通明。
一副缀着青铜片的兕甲立在窗边,寒光映在铜片上,射向四面八方,令人望之色变。
小白身着戎衣短褐,手握羊皮地图,不停揣摩着管仲究竟会从何方发难,不知不觉间竟琢磨了一整夜。
派兵协防莒国,是他与鲍叔牙想出的牵制鲁军的一步棋,迫使鲁国公不得不留下一部分兵力在曲阜,以防齐莒联盟,从东侧偷袭,端了他的老巢。
为着能帮上小白,这几日绿姬也开始苦读太公《六韬》,小白不眠不休,她就待在他身侧,为他添香煮水。
小白时不时催促着绿姬去睡觉,可绿姬笃定了要陪着他,小白既心疼又无奈,只想赶快忙完,好让绿姬回去休息,谁知一下又忙了一整夜。
绿姬起身为小白添水,看着地图上画着的复杂地势,颇为担忧:“假如管仲真的借道卫国,从西边进犯,我们该如何是好。”
小白将绿姬拉至身前,在地图上边比划边说道:“哪有那么容易,卫国公虽然口头答应了管仲,可卫昭伯率群臣竭力反对,称此举会危害卫国安全;驻守济水西岸的卫军将领也拒不领命,甚至加强了巡逻与防范,拒绝鲁军入境。所谓的鲁卫联盟,现在不过成了个笑话,徒给管仲增添几分吹牛的谈资罢了。”
绿姬点了点头,揶揄道:“也是,卫国女公子心有所属,在齐不在鲁,卫国公又怎会真心实意借道给管仲。”
小白眉头微蹙,星眸一转,揽着绿姬的瘦肩,坏笑道:“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?我夫人竟说出这酸话来。”
绿姬推着小白,无奈笑道:“哪里听出酸来,愿意娶谁便去吧,你看我拦你不拦?”
小白坏笑两声,一个横抱将绿姬抱起:“好啊,那我现下就先娶了你吧,你可别拦着。”
还不等绿姬反驳,院门外便传来侍卫大力的敲门声:“君上,姒大夫来的急信。”
小白忙高声应道:“就来”,而后放下了绿姬,低声嘟囔道,“我师父真是成事不足……”
绿姬噗嗤笑出了声。小白迅速拉门出了房间,打开院门,接过竹篾,又关上院门,快步跑了回来。
绿姬赶忙为小白递上一尊温水:“天可冷了,尤其是早晚,你别总不加衣服就出门去。”
小白却无回音,盯着竹篾,神色森然。绿姬看到小白的神情,便猜到了鲍叔牙传信的内容,不由紧张了起来。
小白将竹篾递给绿姬,绿姬定睛一看,果然见竹篾上写着一行金文:鲁军已出曲阜。
心中的滋味说不清道不明,可心跳确实陡然加了速,绿姬明白,小白与纠之间的这场宿命之战,终于要开始了。
小白望着绿姬,心中百转千回,仿佛有千言万语卡在喉头,却不知该从何说起。
绿姬灿然一笑,小手吃力地掂起窗边的兕甲,柔声对小白道:“让我为你穿战袍吧。”
小白一怔,一股暖意铺天盖地席卷而来,他毫不推诿,张开双臂,看着绿姬一点点笨拙地为自己穿铠甲。
兕皮铠甲很重,绿姬小心翼翼地将每一个衔接处的皮绳系好,生恐有任何疏漏,会伤及小白的性命。
系好后,绿姬又逐个将胸口处的青铜缀片抚平,小白的心跳声透过厚实的甲胄传来,绿姬鼻头一酸,眼泪在明眸中不住打转。
强压住离愁别绪,绿姬忍了泪,抬起眼,笑对小白道:“万不要逞匹夫之勇,即便没了这万里河山,你还有我……”
小白满是老茧的大手轻轻拂过绿姬绝美的面颊,星眸坚定如炬:“既要定了这万里河山,也要定了你。”
语罢,小白捧起绿姬的小脸儿,吻上了她的薄唇。这离别一吻意味深长,两人都无比投入,极尽缠绵,直到天昏地暗,呼吸沉重仍抵死相守,不愿分离。
除了温热绵柔的呼吸,忽有如琼酪般微咸的滋味入口,小白一怔,放开了绿姬。她的小脸儿上挂着两行清泪,如梨花带雨,任谁看了都要生起怜爱之意。
小白心如刀割,将绿姬紧紧拥在怀中:“对不起。”
绿姬抬手拭去脸上的泪,强笑道:“你一定要好好的,毫发无损地回来。”
小白应道:“我一定毫发无损地回来,若是缺了胳膊少了腿,我就不回来了。”
绿姬轻捶小白的胸口,呢喃道:“即便缺了胳膊少了腿,你也必须回来。”
小白拉起绿姬的小手,放在嘴边一吻:“放心吧,等我打完这一仗回来,我们就成亲。”
小白不再耽搁,十分不舍地望着绿姬,好像是要将她的样子一笔一划刻在脑中,而后转过身子,头也不回,大步向姝子苑外走去。
绿姬没有跟出去,只是竖着耳朵听着,听到院门开了又关,听到小白马咴叫的声音,绿姬的眼泪再也忍不住,纷纷坠下,颗颗滚落如明珠。
即便有通天之力,却无法预测心爱之人的生死。手心上残存的小白的热度渐渐散去,绿姬含泪望着通天脉,肝肠寸断。